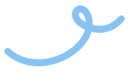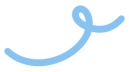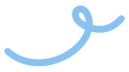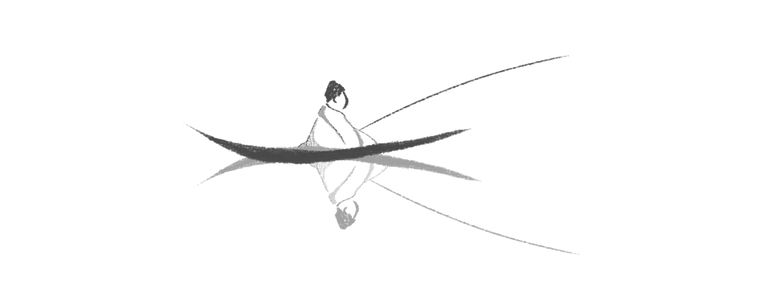如今,不少“美食家”叫人不敢恭维,他们品尝美食的时候,那些故作清高的作派,是在炫耀自身的档次,夸耀自己的品味,显示自己的富有。
许多美食家品尝美食的视频、谈论美食的文章,像是自己正在皇宫进御食,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,让我们这些普通观众和读者产生一种“自己不配”的自卑感。
相反,读苏东坡这吃货谈吃喝的诗文,让人特别亲切和温暖,他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人间烟火气。
读他的《猪肉颂》,仿佛闻到了他身上的油烟味;
读他的《酒子赋》,仿佛又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;
读他的《煮鱼法》,仿佛闻到了他身上的鱼腥;
读他的《菜羹赋》,仿佛闻到了他身上的野菜香。
他自己喜欢吃什么菜,便自己下地种什么菜,自己下厨做什么菜,友人团聚他自己还常常自备酒菜。
他在黄州《与子安兄书》中说:
“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,躬耕其中。作草屋数间,谓之‘东坡雪堂’。种蔬接果,聊以忘老……常亲自煮猪头,灌血腈,作姜豉菜羹,宛有太安滋味。”
去年,我特地去了一次黄州的东坡雪堂,见到堂前“十数亩”荒地,可惜东坡当年的荒地现在还荒着,当地人在上面稀稀落落种了点蔬菜。
“早晨起来打两碗,饱得自家君莫管”,我特别喜欢《猪肉颂》结尾的这两句。在麻城老家吃香喷喷的煨猪肉,我常常也是连“打两碗”,后来在武汉吃藕煨排骨,同样经常连“打两碗”。这两句也让我想起农民工,他们在工地遇上好吃的饭菜,不也是起来连“打两碗”吗?
又岂止是这两句呢?东坡所有谈吃谈喝的诗文都特别近情,煮猪肉就像乡民,煮鱼羹就像渔民,煮菜羹就像菜农,他从来不装不炫不作。恰如他煮的菜羹“味含土膏”一样,东坡本人也散发着泥土的清香。这种泥土气和烟火气,本质是“绚烂之极”“乃造平淡”(《与侄书》),表明他是一个没有任何装点的真人。
他那泥土气和烟火气的大俗,恰恰是极本真极自然的大雅,这就是所谓“大俗即大雅”的深层原因。
估计大家都有相同的经历,心中有事便夜不能寐,精神焦虑则吃饭不香。食欲完全受心情的影响,心情不好会引起内分泌严重失调,而内分泌一旦失调,哪怕山珍海味摆在面前,你都懒得动一动筷子。
为什么不管贬到哪个地方,苏东坡总是胃口倍儿好,吃饭倍儿香呢?
《自题金山画像》写于东坡逝世前两个多月,可以说是他一生的自我总结:
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
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
这三个州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巨大影响?为什么在他心中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?
贬黄州正是乌台诗案之后,苏东坡完全是“向死而生”,他不断对自己进行灵魂的拷问:“长恨此身非我有,何时忘却营营?”(《临江仙·夜归临皋》)
他彻底解脱了功名利禄的束缚,实现精神的蜕变和人生的升华。活着就应当“性之便,意之适”,决意要活出真我。
贬惠州则是年迈远走岭南瘴气之地,此时此刻他不仅超脱了功名利禄,而且已经超然于死生之际,“蘧蘧未必都非梦,了了方知不落空。莫把存亡悲六客,已将地狱等天宫”(《次韵答元素》)。
他在惠州该吃吃,该喝喝,你看他大嚼槟榔,大吃荔枝,大碗喝酒,大口吃肉……
贬儋州更在花甲之年“并鬼门而东骛,浮瘴海以南迁”,当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,都断定东坡“生还无期”(《到昌化军谢表》)。
任何一个人处在这种境地,即使不哭天抢地,也定会肝胆欲裂,哪还有心思品尝玉糁羹?可苏东坡刚到儋州不久,便写信给家乡友人杨济甫说:“某与幼子过南来,余皆留惠州。生事狼狈,劳苦万状,然胸中亦自有翛然处也。”
“翛然”见于《庄子·大宗师》:“翛然而往,翛然而来而已矣。”它是指一种超然洒脱的心境,一种无拘无束的样子。这个吃货连死都不在乎,他还在乎被贬到儋州吗?
东坡中晚年大都在贬谪地度过,但他于人没有怨恨之心,于己没有悲戚之色,因而,《菜羹赋》中“先生心平而气和,故虽老而体胖”两句,便是他的自豪与自道。你要想人老而“体胖”,就得“心平而气和”;你要想“心平而气和”,就得超然于功利,甚至还必须超然于生死。
《景德传灯录》中有一则禅师的对话:
有源律师来问(慧海禅师): “和尚修道,还用功否?”
师曰:“用功。”
曰:“如何用功?”
师曰:“饥来吃饭,困来即眠。”
曰:“一切人总如是,同师用功否?”
师曰:“不同。”
曰:“何故不同?”
师曰:“他吃饭时不肯吃饭,百种须索。睡时不肯睡,千般计校,所以不同也。”
要是为功名所累,为利禄所牵,为生死所困,那就像慧海禅师所说的那样,“吃饭时不肯吃饭,百种须索。睡时不肯睡,千般计校”。
东坡将功名利禄生死全都放下,以使自己“胸中廓然无一物”,此时“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”(《与子明兄书》)。看看他的《与王定国书》:“某其余坦然无疑,鸡猪鱼蒜,遇着便吃;生老病死,符到便奉行,此法差似简要也。”他对于自己的“生老病死”,如此坦荡,如此洒脱,对于“鸡猪鱼蒜”,才会“遇着便吃”,吃着便香。
难怪他既不择时地,也不择食物,“遇着便吃”,一吃起来都放不下筷子:吃荔枝吃出了“厚味高格”,吃鱼羹又吃出了“超然高韵”,吃野菜羹也吃得流口水,吃羊脊骨更吃出了“水平”……